3月23日,药明康德A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17.59万股将上市流通。结合21日药明康德现身沪股通十大成交活跃股,当日净卖出额超过2亿元。截至22日《医药经济报》记者发稿时止,其股价仍在下滑。联系到近段时间其股价的大起大落,不由得让人多了几分遐想。
值得玩味的是,除了二级市场的表现外,大股东行列也发生重大变化:
由药明康德实控人李革夫妇及其两位合伙人有股权关联的WXAT BVI彻底消失在其前十大股东行列。高瓴资本此前间接持有药明康德5%以上的股份。2020年曾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其股票,并成功跻身前十大股东之列,但2021年中报显示,高瓴资本也消失在大股东之列。不仅如此,继多名原始股东首发减持后,近两年共有10名董监高合计减持公司股份超过50万股。
短短数月,资本从不断加持到加速逃离,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?客观来讲,退出,是所有投资者自进场起就等待的时刻。有出有进,属实正常。不过,需引起行业思考的是,医药创新领域热钱退却后,真正的高阶创新如何脱颖而出?
三大变量叠加,谁在抛售白马股?
药明康德最近深陷舆论漩涡,在二级市场颇有“坐过山车”的感觉。
这让很多人难以适应。去年上半年,医药板块整体下挫,药明康德却逆势而上,去年7月,每股更是攀升至172.49元的历史新高,总市值突破5000亿元,上市3年股价翻了15倍。到了下半年,其股价就“变脸”,短短半年市值大幅缩水2000多亿元。截止3月22日,曾经百倍市盈率的药明康德股价已跌至100元上下。
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药明康德的业绩仍表现抢眼:其2021年业绩快报显示,报告期内业绩进一步增长,营收229亿元,同比上年增加38.50%;扣非净利润为40.63亿元,同比上年增加70.38%。
估值与利润悖离,抛开大股东减持的动机不论,这种局面与机构投资者不无关系。
首先,股权结构分散,给批量减持埋下隐患,这也是为何解除限售股票引人关注的原因。
据其财报显示,在40多个股东中,没有一家单一持股比例超过10%。前10名股东有7位是境外法人股东。经历前期资本追捧的暴涨后,就像近期地缘事件持续发酵后的镍价一样,涨幅超出需求基本面后,股权结构分散给资本博弈留下缝隙。
在药审改革、集采、医保谈判等政策驱动下,国内创新浪潮迭起,热钱入局。在MAH制度实施后,CXO这一商业模式被风头正盛的Biotech公司追捧,而传统药企因缺乏成熟的新药研发平台,也在迫切搜寻新突破。相比泰格医药、康华龙成等同行,药明康德的百倍市盈率颇有争议,做多资金需高位套现收割并进行资本格式化。
其次,境外业务占比高。2020年,全球前20大制药企业占其整体收入比重约32.8%。2015-2020年,药明康德前十大客户保留率100%,且业务收入占到93.8%,七成以上来自境外,而新客户的收入仅占6.2%。境外业务比重高及境外原料供应依赖强,均易受到海外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。
上个月,美国商务部更新“未经核实名单”,药明生物两家实体在列,尽管药明康德声明药明生物为独立上市公司,其不持有药明生物任何股份,但仍难平资本恐慌情绪,当日A股开盘1分钟跌停,港股最高跌幅超过27%。
再者,机会红利在转轨。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耗费10年、10亿元的成本,为提高效率,CXO行业应运而生。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是,先行者药明康德赶上国内《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出台,风口上的药明康德,7年后顺利在美上市。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,药明康德股价断崖式下跌。2015年,药明康德私有化并转道A股和港股市场。2018年在A股上市时,股价10.27元,到2021年最高峰的172.49元。
不过,CXO又称“卖水人”,必然会随着国内外创新转型的格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。鼓励高质量创新,就会捅破资本面吹起的泡沫,推动产业链重塑。
药明康德仅仅只是一个典型案例,做多与做空,机构投资者拿捏的尽在方寸间。
值得探讨的是,资本在推动创新升级的同时,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创新力量,而不是像眼下诸多昔日的明星生物医药企业,仍在破发洪流中难以自拔?
能否重回神坛?机会与挑战并存
梳理发现,CXO企业中,除药明康德,凯莱英、泰格医药等在2021年也遭大规模减持。就像此前的恒瑞医药一样,这类企业如何重回巅峰,是外界最为关心的,也是企业面临的最大考验。
归根到底,医药创新终究是实力的大比拼。
当年,美国CXO行业也出现过类似境况。美国CRO公司Medpace选择主要承接First-in-class和best-in-class药物,如全球第一个PCSK9抑制剂、GLP-1等项目,其报价比巨头IQVIA等还要高出三分之一以上,但订单仍络绎不绝,进阶高段位,创新力至上。
解构药明康德的竞争力,同样有三点值得期待:
一是客户结构分散化解了风险。目前其前五大客户总销售额占据全年销售额的20.8%。相对上年,活跃客户新增不少,其通过在中国、美国及欧洲等全球30个运营基地和分支机构为超过5640家活跃客户提供服务。客源广泛且不易受下游钳制,纵向做深具有潜力;
二是业务创新转型释放活力。药明康德始终贯彻执行“跟随分子”的战略,化学业务板块,实现“一体化,端到端”CRDMO业务,订单需求旺盛,推动其2021年全年销售收入加速增长,收入增速同比将近翻番。而测试业务下的实验室分析及测试业务和临床CRO/SMO业务,生物学业务均实现强劲增长;细胞及基因疗法CTDMO业务板块成为业务发展的新支点。国内新药研发服务部业务在2022年将迭代升级,以满足客户对国内新药研发服务更高的要求;
三是商业模式仍具盈利品质。与其说药明康德是CXO公司,实则更像一个平台型公司,在新一轮创新转型过程中,药明康德共享了其实验室和研发团队。截止目前,其科研人员总数超过3万人,高端服务能力输出是其核心抓手。
综合以上三个维度分析,药明康德的盈利品质仍然具备竞争力。
若把视角往前推,CXO行业伴随了中国创新药的从无到有,走向高端。在海外客户和中国成本的双重加持下,大有可为。
其中,部分头部企业还延伸出新的发展逻辑:如这个行业预知项目的成功性更精准,再借助自有资金提前押注,其获益比扎堆在CRO领域和后来者竞争更刺激。药明康德的投资收益,曾一度占到公司营收的三分之二。泰格医药去年出资98亿元参与产业基金,按其上年17.5亿元的净利来算,相当于5年的积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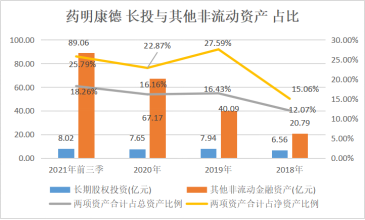
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受访时提出,“医药创新要有长线投资思维,并促进产业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型,引导创新药企跳出传统固有思维、破除研发掣肘。国家层面对于全球新的靶点/药物给予临床资源给予优先权,共同孵化原始创新。”
产业环境在不断进步,“创新转型+国际化”开启第二增长曲线,是产业共性考题。
国家《“十四五”医药工业发展规划》提出,重点推动医药工业创新转型。据统计,2016-2021年我国1类新药申请受理数量逐年提高,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0%。然而前6%的靶点便已囊括了超40%的新药,仅申报并获受理的PD-L1新药就近60款。美国FDA药物评价和研究中心发布的《2021年度的新药获批报告》也显示,全年美国共批准了50款新药,其中27款first-in-class疗法。
国内外创新需求,都给CXO提出更高的要求,速度与成本是比拼的焦点。
由此判断,CXO行业的资源整合将提速,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。资本泡沫戳穿后,横向比价值链人才储备的宽度,纵向靠创新能力的深度。
如药明生物,构建的护城河在其研发能力,尤其是新工艺技术开发的项目需要足够强大的研发能力。其ADC技术平台、双特异性抗体技术平台等专利技术平台/独具优势。据悉,在全球获得40个ADC项目。
后记<<<
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,才能在创新转型新浪潮中获益,如规模没有药明康德大,仅为其十分之一左右的昭衍新药,但在毛利率方面远超一众CRO巨头。究其原因,昭衍新药从事的临床前药物安全性评价市场壁垒高。目前国内仅有包括昭衍新药在内的两家CRO获得准许进行全部十类药物GLP研究所需的证书。
当然,CXO行业也面临共性考题:一是对于大型创新药企而言,随着外包费用的节节攀升,自建临床团队成本反而更低,质量也有保障。如百济神州、恒瑞医药开始自建CRO团队。二是企业本身研发投入仍有待提高。2020年,龙头企业药明康德年研发投入人民币69325.96万元,较2019年增加17.42%。可想而知,很多中小CXO企业在创新方面也是挑战。
为原创性新药企业助力,CXO行业同样需要在创新上拼速度。



